詩 是一種崇高的藝術形式。 它知道如何讓我們接觸到我們內心並不總是可見的宇宙。 多虧了它,我們學會了通過美的棱鏡觀察世界,與我們努力接受的東西和平相處。
保羅·甘比(Paolo Gambi,詩人、作家和博主)的詩歌被稱為 治癒的詩. 自 2019 年 2012 月起與 Italiani.it 合作,他獲得了 Guidarello 作家新聞獎(2016 年)、里米尼歐洲獎(2019 年)和 Loris 詩歌獎 Malaguzzi 獎(XNUMX 年)。 他寫過 28書 並與紅衣主教 Tonini、Gustavo Raffi、Alessandro Cecchi Paone、Alessandro Meluzzi、Ettore Gotti Tedeschi 甚至 Raoul Casadei 合作。 最近他出版了詩集 寄居蟹的謎,玉蘭的記憶,鮭魚的登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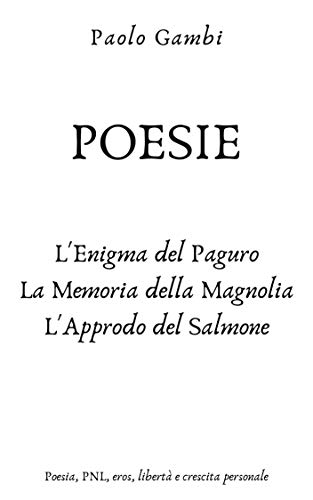
它不僅僅是一個收藏品,更是一次探索之旅,走向靈魂最隱秘的著陸點。 閱讀甘比的詩歌是一段旅程。 但也有機會看到能夠感動世界的純粹的美觀念。
很多都是甘比筆下關心的話題。 在謎團和情緒之間移動將是輕鬆而美麗的。 邀請按照個人理想生活,不懼怕 逆流而上. 永遠不會中斷我們的個人搜索 . 賦予生命的解毒劑 液體地獄 它向我們隱藏了事物和生活的本質。 Paolo Gambi 在這次獨家專訪中談到了詩人的角色和美的關鍵概念。

是什麼激發了你的線條?
他們在尋找我,而不是相反。 了解藝術的人都知道它是這樣運作的:它決定一切。 當你出現時,你只能屈服於它,或者你餘生都會後悔沒有這樣做。 這就是我放棄一切的原因:新聞、工作、正常生活的想法。 讓自己被藝術追逐,讓線條自己流淌。
詩歌對你有什麼價值?
詩歌是我必須將美的奧秘翻譯成人類語言的方式。 它是一座橋樑,就像任何形式的藝術一樣,將遙遠的世界、這裡的事物與彼岸的事物、別處連接起來。 我會說詩歌是 一切今天為我準備。 我真的相信它可以拯救世界。 確實,我認為它已經在這樣做了.
今天詩人的角色是什麼?
有些詩人堅信自己是詩歌的主人和監護人,他們處於“深奧”的知識中,處於封閉的非常小的圈子中,確信只有他們才能處理詩歌。 我恰恰相反,我深信沒有人可以稱得上藝術的“大師”,最多只能稱得上是他的僕人。 作為藝術的僕人,詩人必須將詩歌帶到任何地方。 今天的詩人,在一個歷史時刻,在這個歷史時刻,文字——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也由於技術而重新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們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將詩歌,因此救贖,帶到新的集體無意識中,在頭腦中它反映了整個地球村。 這不是一件小事,只有弄髒你的腳和手指才能做到。
我們從您的收藏中註意到對人類靈魂的仔細了解。 你的興趣是如何開始的?
當我意識到我屬於“人類”類別時,它就開始了。 作為一名記者,我多年來一直在追求人類的興趣,講述人們的故事。 然後我開始在我的小說中編造故事。 然後我以“心理教練”的身份進入人類思維的迷宮。 但是,只有藝術語言才能完整地給出答案,這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向人們闡明人類的奧秘。
你的收藏是 拯救世界的美麗之旅. 你的想法是什麼 ?
對我來說,美是絕對的東西之一,它是一個神秘的概念。 是的,當然,美在小事中出現,它被反映,即使只是片刻,在一張臉,一個身體,一個風景中。 但它遠不止於此。 美、善、神,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同義詞,是人類用來講述僅憑他們的思想無法接受的東西的詞。 美是存在於內心法則生效的神秘維度中的東西。 但它不會在未來拯救世界。 它已經在這里和現在保存它。
寄居蟹試圖將自己從存在的地獄中拯救出來。 什麼東西能讓我們安全?
我不覺得自己是很多答案的承載者,對我的問題發表意見是我最擅長的。 我知道我們生活在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所說的“液體地獄”中,在齊格蒙特·鮑曼那裡,一切——身份、制度、意識形態——都被液化了。 為了能夠自救,我們需要木頭和殘骸來支撐。 如果這棵木頭找到了土地,它就會復活並變成一棵樹。 樹保存著宇宙的記憶。 這是本書的第二部分,“樹棲煉獄”。 所以也許第一個讓我們遠離地獄的液體邏輯的詞是“記憶”
你的一首詩致力於寬恕的藝術。 沒有寬恕,就只有地獄。 我們如何學會寬恕,它可以改變我們多少?
那些不知道如何寬恕的人,最後總是會因自己的判決而受到一個非常傑出的譴責受害者:他自己。 為了原諒別人,我們首先要學會原諒自己。 帶著謙卑的擁抱,接受我們不喜歡的一切,所有不符合我們思想的東西。 為了放棄邏輯上正確的東西——即對有罪者的定罪——任何想要寬恕的人都必須找到兩顆小種子:謙遜和擁抱。
在你的收藏中有你最喜歡的一首詩嗎?
有一些台詞今天仍然讓我感動,當我讀到它們時。 像這些:
並且只剩下重要的: - 只留下重要的:
什麼是小 - 什麼是小
而且進展緩慢。 - 並慢慢走。
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其他人不會說什麼。 詩歌就是這樣:它與人們親密交談,而每個人本身就是一個世界。
三文魚設法將自己從地獄中拯救出來,因為與其他人相比,它超越了大眾所能做的。 逆流而上對你意味著什麼?
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強加的“正常”。 今天,政治正確者改寫了新的教條,以指導渴望成為獨特的新意識形態。 在這裡,今天逆流而上意味著例如為自由而戰,反對政治正確的暴政。 但這也意味著與自己作對。 要成為真正的自己,我們必須能夠放棄許多我們認為是我們一部分的東西。 就像堅果:要到達心臟,你必須打碎外殼。
大流行有利於內省。 以及你的台詞讓讀者陷入自我。 內心對話對於創造性目的有多重要?
我失去了內部和外部的輪廓。 對話是內在與外在,我與他人,我與我自己,以一種幾乎模糊不清的方式。 “對話”是一個非凡的術語:來自希臘語 dia-logos,一個跨越的詞。 在這裡,我相信我們的挑戰,每個人的挑戰,正是能夠向這個詞敞開心扉,向這個包含整個宇宙的“對話”敞開心扉,從最遙遠的星星到我們鄰居的花園。 正是從不同事物的相遇中誕生了新事物。 創作過程就在那裡
詩歌是一種難以自我表達的藝術形式,你怎麼看?
我認為這並不完全正確。 我很高興地看到,社交網絡喚醒了被詩歌吸引的新一代。 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和非常年輕的人——僅在意大利就有幾十萬人——他們將 instagram 用作簡單詩歌研究的視野。 在隔離期間,我以很小的方式進行日常詩學。 每天晚上 9 點,我們閱讀大大小小的詩人。 一開始我們是二十歲,然後是五十歲,然後是幾百歲。 我們已經達到了2400人。我相信,近幾代那些想把詩歌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神秘學界的事情的詩人確實讓人們遠離了這種藝術。 但那個時期已經結束。 門重新打開,空氣重新流通。
我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帶進了我們鼓舞人心的老師。 你的是什麼?
我總是說那些在社交網絡上給我寫詩以閱讀他們的詩的人說:“要寫一首詩,你必須閱讀一百首詩”……因此,這份名單會很長。 不過,我要提一下要對付詩歌就忍不住要知道的三個神聖怪物:荷馬、但丁和莎士比亞。 我特別提到的一位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我看來,他什麼都懂。 然後是 Szymborska,因為他是最早將我帶入詩歌世界的讀物之一。 還有佩索阿,儘管他的悲觀情緒會讓他離人類如此遙遠,但他在我身邊跳動著。 比意大利人少得多:目前(而且每天都在變化)我覺得與 XNUMX 世紀的意大利詩歌有些距離。 除了繼續讓我著迷的鄧南齊和昨天也讓我落淚的帕斯科利。





